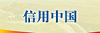1954年以前,在巨龙岗地区,有一个远近颇有名气的村庄叫楼房湾。其他村庄普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土筑泥砖墙,芦苇杆子夹壁,茅草或稻草盖顶,阴湿低矮的房子,而楼房湾的房子就大大的不同了。那里的房子全都是青瓦盖顶,青砖灌斗墙,又高又楼,像楼房一样,因此人们把这个村庄称为楼房湾。其实,楼房湾的楼都是无门无窗,只能藏物,不能住人的暗楼。这个湾子大约在清康熙王朝后期形成雏形,到嘉庆帝时就有了一定的规模,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到了道光咸丰之间,已形成了今人所见到的楼房湾村了。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村庄,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惜的是在1954年的特大洪水中荡然无存了。
整个楼房湾的房屋都是坐西面东,依岗顺坡布局。湾子中有几条深巷,有些巷口修有门楼,门楼上悬有“司马第”、“荣禄第”、“观察第”……等横匾,不言而喻,湾里住的都是仕宦人家。巷内的房屋一般都是三间上下堂,劣马回头的格式,一进门就是大天井,天井上下是架梁的四大壁的正厅和对厅,既高大又宽敞,能同时开八张席。有的房屋是四间上下堂的,第四间的中间也有个小天井,天井上是书房,下边是家庭教师的起居室,天井中间一般都砌有花坛。全湾最大的房子是曾经当过清末右江兵备道(整饬地方兵备的道员)的刘谦三做的。他的房子的正厅面积就有上百平方米,对厅是戏台,遇有喜庆活动,就在正厅宴客,对厅唱戏,听说汉剧名演员余洪元、李彩云、大和尚、牡丹花等都曾在这家的戏台上演过堂会戏。
楼房湾的住户都是仕宦人家,没有一户是种田的。封建帝王时代实行科举制度,湾里出了不少秀才、举人和进士。清代道光帝时任国子监学正的刘传铭(字椒云)就是楼房湾的人。听说刘传铭中举后赴京会试前,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店,结识了以后成为清朝大臣的曾国藩和龙启瑞,成莫逆之交。刘椒云先后三次参加会试,恰巧主考官就是曾国藩和龙启瑞,为了避嫌,他放弃了会试,发生了“三辞会考”的故事。后以举人(破格录用)入仕,终其生。逝后,曾国藩和龙启瑞都为之书赠有牌匾和石碑,对他表示哀悼。
科举时代,楼房湾家家请有家庭教师,男女都读书。男青年为了“学而优则仕”,青年女子读了书则显得自己有才华。一般青年男女都通音律、工诗词,而且喜欢唱和。
书香子弟,诗词曲斌、琴棋书画都有所学,即使在平日的生活中有时也文来文去,别有一番情趣。据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和和睦睦,夫唱妇随,生活美满。一日,娇妻轻弹棉花,打算搓出棉条纺线,夫君则陪伴在旁观看。搓完棉条,妻子掸去身上的花尘,笑着对夫君说,我即兴口念一阙《忆江南》你听听:“飞花起,满屋弄轻毯,偷眼评猜郎意思,怕郎笑我早白头,急望上妆楼。”丈夫听完忙赞道:“好词,好词!”当即随和一阙:“飞花落,香汗湿衣裳,雪里红梅添秀色,淡抹风韵胜浓装,底事盼梳妆?”二人卿卿我我,柔情相视良久。
湾子的后面有个瑞竹堂书屋,那是清国子监学正刘椒云的老家,高大的暗楼上堆满了藏书。据说这批藏书都经过刘椒云评注,其落款均为“刘椒云通眉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惜刘椒云的后代早去东北定居,留下的藏书无人管理。后来请了一位太婆看门,这太婆是刘椒云的侄孙女,很有学问,深受人们尊重。她总不让人上楼看藏书,哪怕是自己的堂弟进士刘作雄。有人曾看到太婆请人上暗楼屋顶捡瓦,可能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雨,也可能是晾开透透阳光,除去霉气。太婆叫什么名,何时担任照管瑞竹堂,当时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些情况无人知晓,只是传说。但从刘椒云去世的年代(1849年)算起,到清王朝退去历史舞台相去六十多年,如此算来这位太婆可能是在民国初年被请去看屋,称她为太婆也应该在五十岁以上了。到1933年汉阳县县长邓炳得知瑞竹堂藏书的情况,特地派专人到驻龙乡会同联保主任到瑞竹堂拜访老太婆,要求查看一下藏书,以便采取保护措施,以后动员太婆组织人员翻晒藏书,均被她婉言谢绝。直至1952年土改时,工作组领导群众将瑞竹堂的藏书全部转移到乡政府封存起来。
后来听说这批藏书,于1954年特大洪水之后,经曾在山东师范学院工作的楼房湾的刘氏后裔致函湖北省图书馆,请求保护瑞竹堂藏书。省图书馆及时派出专人同汉阳县文化馆干部刘正敏到驻龙乡,在当地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将瑞竹堂尚存的古书运到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