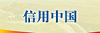阅读提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存在差异与张力,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修复”的良性互动,即“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自然不仅具有提供物质资源的工具价值,更具有自身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存在价值。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赵继伟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认知,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以《文选》出版发行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联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沙及各类生物、环境要素等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人类是这个相互联系的自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于自然之外或者凌驾于自然之外的“旁观者”“主宰者”“统治者”。因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与儒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思想是一致的。
从物质本源来看,人类由自然物质演化而来,人类的生命活动和衣食住行都始终依赖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离不开阳光、空气、水、土壤、矿产等自然要素,也离不开自然提供的各种物质能量。“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要素或环节被破坏,都会引发系统性、连锁性的反应,造成生态危机,最终威胁人类生存根基,反噬人类自身。比如,生物多样性减少会影响生态平衡,进而制约农业、医疗等人类发展所需的资源供给,水土流失导致农业减产、气候失衡引发极端天气,等等。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认识到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为此,需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存在差异与张力,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因而,发展与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会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这种改造可能打破自然原有的平衡;而自然也有其客观规律性,会对人类的不当活动施加“反作用”。同时,人类的“改造”不能脱离自然规律,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同时,自然的平衡也需要人类的主动维护——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修复”的良性互动,即“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根本上否定了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发展模式,也否认了“以牺牲环境换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逻辑,强调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摒弃“先发展后治理”“人类与自然对立”“杀鸡取卵”式的旧思维,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的承载能力,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确保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一方面,“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潜力所在。只有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发展能为生态保护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生态环境投入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只有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让发展成果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追求“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从“对立”走向“统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对自然的价值认知,将生态价值提升到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实,自然不仅具有提供物质资源的工具价值,更具有自身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存在价值。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文明的视角看,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整体性意味着,生态价值是经济价值的前提与基础,经济价值是实现更高生态价值的手段与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不可分割。
生态是文明的根基,决定着经济价值的上限。人类文明诞生于自然生态系统,空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材料库”和“垃圾处理厂”。一旦生态系统崩溃(如水资源枯竭、土壤沙漠化),依赖其存在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将失去根基,经济价值便无从谈起。这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因生态破坏而衰落的案例中得到印证。
经济是文明的动力,反哺着生态价值的提升。健康的经济活动能为生态保护提供技术、资金和管理支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例如,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产业,既能获得经济收益,又能促进生态修复;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能有效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文明升级要求二者从“对立”走向“统一”。在工业文明早期,人类以“征服自然”为导向,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对立起来,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会带来诸多问题。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得到了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通过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来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最终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延续。
生态治理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公事”
生态问题的全球性与关联性,决定了这个问题必须通过人类协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即生态问题需要人类协同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决定了应对责任的不可分割性,人类需超越地域、国界与制度差异,以“地球生命共同体”意识共同守护唯一家园。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要参与生态保护的行动当中,共同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不受国界、地域和制度的限制,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生态问题的“无国界性”是责任共同性的前提,任何国家的局部行为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影响。例如,某一地区的工业污染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扩散至全球;亚马逊雨林的砍伐会影响全球碳循环与气候平衡;极地冰川融化则威胁所有沿海国家的生存安全。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性,决定了生态治理不是单个国家的“私事”,而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公事”。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作为地球共同体的责任,超越了国界、地域和制度的差异,要求人类以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树立全球生态治理意识,通过国际合作、协同行动,共同承担起保护地球家园的责任,共同参与保护地球家园的行动中。发达国家因其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生态“欠账”更多,且具备更先进的技术、更充裕的资金与治理经验,应在减排目标、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因而需要承担更多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发展中国家在保障自身发展权的同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探索绿色发展路径,避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重要的是,生态治理责任的共同性最终需通过具体的全球合作落地,这要求各国超越短期利益与地缘政治考量,通过多边机制达成共识、制定规则;通过技术共享、资金互助帮助欠发达地区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民间组织、跨国企业、公众的联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参与的全球生态治理网络格局,共同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作者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